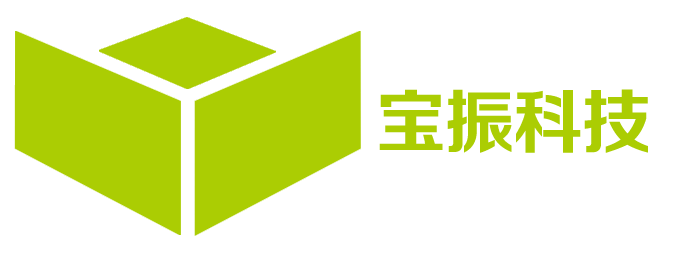- 2023-10-28 垂直綠化植物墻除視覺效果的作用外其他作用
- 2023-10-28 戶外垂直綠化墻立體花盆適合種什么植物
- 2023-10-28 道路立體綠化組合花盆在道路綠化中的使用
- 2023-10-27 城市綠化建設走向立體綠化組合花盆空間
- 2023-10-27 辦公室打造垂直綠化植物墻可緩解員工壓力
城市:生活的藝術與藝術地生活屋頂綠化種植模塊 廈門寶振科技
330多年前笠翁李漁完成的《閑情偶記》一書成了暢銷書,有精美圖文版、還有經典圖說版。據說喜歡李漁的人也越來越多,從“抓革命促生產”到“發展是硬道理”,再到今天開始關注生活樂趣,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歷史進步。
余秋雨先生在《重讀李漁叢書》序言中寫到:“中華文明在本質上是崇花墻花盆實避虛的,但在它斜屋面綠化花盆以后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反而產生了一種倒逆性代償,即不少文人避實崇虛,不愿或不擅對生活實物進行文化關照了”。果真如此的話,如何認識城市、看待城市文化、關心城市生活的問題倒是值得談一談了,而將城市作為時空藝術、公共藝術和生活藝術來研究也可成為極有趣的話花柱容器題之一。
一、誰需要“皇帝的新衣”?
我們的城市在喪失特色之后,都想要以建造紀念碑式大建筑的方式,盡快使城市重振雄風、改變面貌。然而城市是一個整體,如果到處都是亮點,也會讓人無法忍受,甚至產生厭惡感。
以首都北京為例,保護老北京城的問題爭論了50年,至今并未形成共識,這不能不說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而在《北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中明確制定了“整體保護”的方針后,一個體量驚人的“巨蛋”,作為“國家大劇院”,即將戲劇性地誕生于傳統中軸線西側。這個“巨蛋”的體積龐大、輪廓醒目,與北京的空間尺度、傳統肌理、城市形態格格不入。
庫哈斯的CCTV大樓方案除了帶給人們震撼之外,沒有任何新東西,在大談可持續發展和科學發展觀的今天,為了這一視覺上的“震撼”,工程建設和運營管理將付出非常昂貴的代價。國家體育場的招標,由兩位國際大師——赫爾佐格與德梅隆共同構思的巨大“鳥巢”方案獲勝。評委之一庫哈斯認為:這一建筑也許是中國人無法想像的,但確實只有中國人才能建造。但是,這個被《南方周末》稱為最昂貴的“鳥巢”,在容納10萬人的巨型體育場與溫馨的鳥巢之間,極為基本的建筑尺度問題如何能夠解決?
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兩院院士吳良鏞先生認為:短短不足20年盡管房子建了不少,但是“千城一面”,這些未經消化的形式主義舶來品破壞了城市的文脈肌理;為了尋找和塑造特色,決策者不顧一切地推介形象工程,熱衷于“有想法”和“不—樣”。通過“國際招標”推出的各種千奇百怪的城市規劃和建筑設計方案告訴人們,合理的一般都不行,不問功能造價,只要“新奇”就行。
因此,中國的一些城市成了外國建筑“大師”標新立異的“試驗場”。一個城市沒有“大師”作品似乎就是天大的遺憾,評委如果不附和就沒有水平。“皇帝的新衣”這個古老童話,成為中國城市的時尚肥皂劇。
二、“建筑面前人人平等”
作家趙鑫珊先生近年來對建筑文化表現出極大的關注,他獻給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新著《建筑面前人人平等》,告訴我們一個極其簡單、但是又極為重要的真理:在建筑面前也需要人人平等。上述那些所謂的實驗性、先鋒派作品,大多是首長工程、形象工程、獻禮工程。“公款追星”現象,一些媒體給予曝光和批評,而為官一任,一定要在城市里留下劃時代的“紀念碑”,而且還要將自己的審美觀甚至嗜好強加于上的行為卻極少受到應有的批評。
建筑作為“不可抗拒的藝術”,其投入之巨大、影響之久遠,一般人難以想像。有人說:安德魯的“國家大劇院”報了華裔建筑師貝聿銘巴黎羅浮宮金字塔工程所謂的“一箭之仇”,對此評說,本人一直是沒法理解的。如果說羅浮宮改建工程是“錦上添花”,“國家大劇院”工程則只能說是“傷口撒鹽”,是保羅·安德魯主張“保護一種文化的惟一辦法就是要把它置于危險境地”的“無禮取鬧”。
事情到此也就罷了,糟糕得是故事還沒結束,在各場轟轟烈烈的鬧劇熱情獻演時,建筑大師貝聿銘終于也無法耐住寂寞,85歲高齡重新出山、設計蘇州博物館新址,明知“這塊地很重要,特別有挑戰性。文化保護區就在里面。拙政園在新館址的后面,忠王府在它的左面,在這里搞建筑不容易。”還是在故鄉的土地上,過了一把癮。
為建造這一有特殊身份的“中而新、蘇而新”的“圣地”建筑,“世界文化遺產”、“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等重要歷史紀念物,在不平等的狀態下遭遇挑戰,另外兩處保護建筑被迫整體移建,一般民居只能是一拆了之。
即便是建筑大師或老資歷的建筑權威,也不應忘記,城市建設規劃是建立在那座城市特有的歷史條件、時代需求、人文背景等基礎之上的,應綜合城市獨具的市民心理、審美情趣、風俗時尚等諸多要素。
歐美城市對城市景觀和歷史環境的保護,都是通過嚴格的城市規劃控制來實現的。沒有約束,其實是不會有真正的創造的。只有當城市遠離了執政者的權力控制,成為非全能之物,并實實在在為市民而建設時,才會出現真正意義上好的城市設計。
在全球化過程中,地方意識和本土化逐步獲得重視,尤其是以喚醒社區公民意識和公眾參與為主軸的“社區營造”運動正方興未艾。城市公共藝術的營造與發展,應以社區參與和公共化精神為出發點。
三、“懷舊熱”掩蓋下的文化“墮落”
城市作為人與自然共同創造出的作品,是一種典型的文化景觀。除少數例外,都是長期歷史發展而形成。因此,它有豐富的內涵。城市的各種建筑,不單純是為某種用途而建造的,它也反映一種藝術美。在整體或局部,呈現出一種文化上的意識。
今天,“城市已不再作為生產的一種組織方式,而是成為一種消費中心;它們也不再作為空間位置和歷史事件的網絡點,永久地失去了作為流動的公眾生活的空間這樣一種地位。”
從表面上看,1990年代的社會時尚充滿了一種古色古香的氣息,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變得很懷舊、很有歷史滄桑感了,對舊時代之夢幻沉迷不已。老照片、老房子、老電影、老唱片、老漫畫……簡直到了逢“老”必火的熱度。這種懷舊,是因為現實中歷史環境、文化遺產消失得太快,人們無能為力只好個人收藏花球容器起“歷史”?還是為了將來的升值,把公共的歷史文化盡可能地占為己有?沒人考證過。只知道,城市中越來越多的“文化老街”——唐宮、宋城或明清街,不過是影視化的建成環境,充滿虛偽的氛圍和功利的意圖。在清宮劇戲說歷史的同時,明清街和人造景觀也在偽造“歷史”和糟蹋文化。
上海“新天地”開發的成功,讓城市建設的組織者和房地產投資者都看到了“歷史”的經濟效益,但是“新天地”更像是歐洲小城里某個溫馨的廣場,與老石庫門其實已經沒什么關系了。“新天地”不過是由老石庫門改造成的供外國人觀光和白領階層休閑的酒吧區。走在其中,我們無法聽到歷史的呼吸,感受到傳統的脈搏。
近年來,城市的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經過大規模的更新改造,“一個個破落而個性尚存的城市仿佛不約而同地涌進同一家美容院,出來的時候已是清一色的珠光寶氣、油頭粉面。”普通老百姓感覺自己居住的這個城市越來越陌生,作為家園的感覺越來越淡薄了。城市正成為人類最大的超級欲望場。
不僅如此,在舊城改造中,經歷了大規模的疾風驟雨式的開發,多少歷史街區幾乎是在轉眼之間就在城市中永遠消失了,大批大批的老居民離開居住了幾十年的家園,帶著留戀帶著無奈,取而代之的是貴族化空間和鍍金的文化。
四、別再把老房子當作“臭襪子”
一個城市沒有了人,沒有了普通人的生活,也就沒有了真正的地域文化或社區文化的存在。城市人的生活方式、日常生活環境構成了一個社會賴以存在的基石,構成了市民生活的文化生態。文化生態對于人類生活來說,是和自然生態一樣重要的事物。歷史建筑、歷史街區是城市設計中的景觀資源,是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文化資本,是保持城市特色的物質要素。
多年來,我們一直把四合院、里弄住宅等普通民居構成歷史環境,當作舊城改造的對象,將歷史建筑當作危舊房對待。形象地說就是把普通老房子當作了“臭襪子”。
青年作家、批評家余杰在文章中說“人們總是厭惡臭襪子,把它們扔到床下。其實,襪子有什么錯呢?臭的是自己的腳,襪子不明不白地充當了替罪羊。”同樣地,老房子的破舊不堪,都是人們不當使用、過度使用造成的。
而且,居住擁擠、住房衰敗的問題是經年累月形成,要解決它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大部分居民屬于中、低收入階層,這種情況是具有普遍性的。因此,改善舊城居住環境的最大困難還是經濟問題。把一個需要經過相當長的時期才能實現的社會工程,當作要在一個短時期實現的建設項目來做,顯然是不妥當的。即便是用推土機趕走所有的人,但貧窮依然存在。城市的貧民區也只是轉移了,并沒能消除。
北京“南池子”工程的本來出發點可能是想進行一種歷史街區保護更新模式的探討,在保留歷史韻味的同時改善居民的生活質量。人們感到失望是因為破舊的棚屋消失了,可那些古老的四合院也一起消失了。南池子地區是北京歷史文化名城的歷史文化保護區之一,它的居住條件比內城其他地區要好得多,人均居住面積近7平方米,幾乎是北京內城統計數字的兩倍。
如果政府在今后改造舊城區的工作中推廣這種自認為不錯的“南池子”模式的話,那么,北京就會最終失去它作為一個古老的文化名城所特有的魅力了。導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城市歷史風貌的缺失,城市記憶的不連續,城市文化隨老建筑、四合院的消失而流逝。在北京市提出“人文奧運”和“皇城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目標的今天,南池子改建工程不能不說是極大的遺憾。
在舊城更新改造過程中,徹底改變整個舊城破舊的面貌的思想觀念,大拆大建、推倒重來的“脫胎換骨”改造方式,正是出現城市特色危機的直接原因之一。而將歷史環境保護、歷史街區整治改善,演變為舊城更新改造,可能會成為在大規模“建設性破壞”之后的、新一輪的“保護性破壞”,對歷史街區的打擊將是無可挽回的,也是毀滅性的。
五、“深入生活”設計城市
在城市開發建設中,生活質量才是最重要的。在城市現代化的過程中,高質量的生活是必不可少的。城市美最為重要是生活美,現實中的生活是真實的、靈動的。社區中那些細微的事物,街道上所有的一切,生活環境中潛在的東西,它們也許并不亮麗、并不時髦,但卻可以推動真正的社區文化的營造。胡蘭成在“隨筆六則”中談到:“以前到過的名勝印象都很淡,倒是常走的小街小巷對我有感情。我游過西湖,見過長城,可是動人的只是當時的情景,不是當地的風景。……小時候的為風景所動其實就是努力使自己感動。”只有日常生活,才讓人感覺到真實。
美國著名建筑理論家Christopher Alexander認為:“城市并非樹形”。城市是一種不斷變化的場景、事件和交往組成的網絡,一種交換和發展的系統。城市需要盡可能錯綜復雜并且相互支持的功用的多樣性,來滿足人們的生活需求。簡單地說,過于規整劃一的城市空間,往往缺乏魅力。“凌亂一點才是家”,光彩華麗的往往是“樣板房”。
設計必須因地因時因人而異,以一種新方法取代風格的變化。過去,“深入生活”是對文藝創作的基本要求。今天,越來越多的建筑師不愿意將自己從事的建筑設計工作稱為“做方案”或“畫圖”,更愿意稱之為“建筑創作”,而在所謂建筑創作中卉花盆活動中,最為缺乏得恐怕就是“生活”:對生活的了解、對生活的尊重、對生活的關愛。
正因為如此,Nigel Coates在“街道的形象”一文中提倡:“生活本身是真正的建筑,……讓我們運用生活來進行設計吧!”